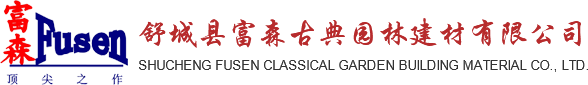新闻中心
让非遗传承“活”在当代“耀”在千秋
发表时间: 2025-01-23 来源:新闻中心
11月5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实施情况的报告。
报告显示,目前,我国非遗资源总量近87万项,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0万余项,其中国家级代表性项目1557项。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作执法检查报告时指出,自2011年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实施以来,国务院及各部门、各地方积极践行立法宗旨,认真落实法律规定,采取有力措施推动非遗保护和传承取得很明显的成效。一大批体现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遗项目得到有效保护,非遗工作体制机制不断健全完善,非遗保护理念持续深化,非遗服务当代、造福人民的作用进一步发挥。
从5月到8月,检查组深入146家非遗传习场所、非遗展示场馆、非遗工坊、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非遗特色村镇和街区、学校及相关企业等单位进行实地调研,与200多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面对面互动交流,72名全国人大代表参加有关活动。
“参与执法检查很受震撼和鼓舞。非遗就像一个色彩斑斓的大花园,历史厚重、灿烂辉煌,令人目不暇接。”“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植根于中华大地的活态文化,是发展着的传统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它是存在于生活之中的活的内容。”“非遗不是民间传统文化的简单重复和模仿,而是结合当前、面向未来的创新、创造和再生。”……在对报告进行分组审议时,常委会组成人员普遍认为,本次执法检查坚持正确方向、聚焦检查重点、突出问题导向、丰富检查形式、广泛听取民声,全面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实施情况及成效,深入分析面临的问题和任务,并为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全面有效实施提出下一步工作建议,让非遗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非遗似繁花,每一朵都有其特定的土壤和生存空间。设立文化生态保护区,加强系统性保护,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程中保护理念和方式的重要探索与实践。
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田学军介绍,自2007年以来,我国已设立23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还有210多个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区域性整体保护正在探索推进。
“任何一项非遗绝不是孤立存在的,它的产生、存续与周边整体的生态必然有内在的关联性。”田学军认为,保护传承非遗必须深刻理解“见人见物见生活”这一重要理念,从生态的角度来推动非遗项目保护与相关文化空间整体保护。他建议,从文化生态理念出发,强化整体性保护,继续探索“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从单一的项目性保护过渡到关注与非遗项目所孕育、存续发展的人文生态和自然生态,从而达到实现整体性保护的目的。
各民族优秀民间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非遗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相互交流、共同智慧的结晶。鹿心社委员认为,非遗保留了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记忆与中华文化基因,是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生动实践,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他建议,在非遗保护中要加强系统性保护,维护非遗的完整性、连续性,注重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通过非遗保护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认同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非遗保护是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涉及交叉学科的多方面知识,如历史知识、考古学知识、自然科学知识等。”汤维建委员认为,现在高校要倡导推动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学这门课程,使非遗保护人才辈出。还要强化非遗工作坊等机构对非遗高质量人才的培养。要让非遗进入大众视野,让非遗保护成为人们认可的比较优质的职业选择。
目前,修改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已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张勇委员建议,根据非遗保护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结合报告指出的问题和不足,扎实开展修法前期调研工作,全面总结实践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强化非遗系统性保护和制度创新,积极推进修法工作进程。
执法检查了解到,一些非遗项目主要依靠师徒间“老带新”、家族式“传帮带”、口传心授等方式传承,时间长、见效慢,在现代生产生活中应用场景不多,年轻人学习的积极性不高,传承人老龄化现象较为突出,面临后继乏人的风险。
李巍委员参加了执法检查全过程,通过到10余个省参加实地调研和检查抽查,他深感非遗传承人老龄化问题要引起高度重视。“首先要完善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制度和体系建设,构建多元化的认定体系和模式,既要认定代表性非遗传承人,也要扶持一线一般性传承人,形成代表性传承人、‘候补’传承人、‘潜在’传承人的三级非遗人才梯队。”此外,他还建议,要加强对代表性非遗传承人的评估和动态管理。
郑建闽委员发现,部分非遗代表性项目传承比较困难,尤其是一些经济效益比较低的非遗项目,传承环境很差。传统的师徒传承、家族传承越来越难以适应非遗保护的要求。同时,职业技术教育等新的传承人培养模式还难以满足实际需要。他建议,进一步加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和管理,安排专项经费对濒危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开展授徒、传艺、交流等传承活动给予支持,持续壮大传承人队伍并提升传承能力。
“现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仅对国家级、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及认定代表性传承人作出了具体规定,对市、县两级没有相应规定。”郑建闽建议,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修订时,增加对市、县两级政府建立本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及认定代表性传承人的相关规定。
段春华委员强调,要重点加强青少年传承人的培养,教育引导青少年更好地认知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激励更多的青少年积极投身于非遗保护传承队伍。要进一步发挥高校资源优势,鼓励有学科优势的大学增设非遗专业,支持非遗人才开展研修访学、展演展示,大力培养一支奋发有为的非遗保护传承主力军。
在优化人才培养方式方面,李巍建议,加快构建面向各个年龄段的非遗教育培训体系,建设“学徒—技工—工匠—大师”四级传承人激励机制。统筹资源、广开门路,设立专项资金支持非遗技艺人才的培养,尤其是要加强青年队伍培养。还要深化高职院校和企业之间共同培养非遗传承人的长效合作办学机制,支持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参与授课和教学科研,重点培育非遗保护与传承的复合型人才。
方向委员关注到了非遗传承人激励机制完善问题。“不少非遗传承人面临收入低、生活困难的问题,无心传承;有的生活方式改变,不愿传承;还有一些缺少人文关怀,不想传承等等。”他建议,在现有激励措施的基础上,探索完善非遗传承人作出贡献与授予荣誉相关联、年度评估与资助资金相挂钩的激励措施,进一步提升非遗传承人的传承责任心、工作投入度和事业成就感。
“目前有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遗产,不能动,动了就不是遗产了,创新是另一回事’的观点,这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保护以及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影响力极为不利。”全国人大代表地力下提·帕尔哈提认为,非遗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源自世世代代的传承人在继承基础上的再创造,使其所传承的项目能够与时俱进地传延发展,满足不同时代人民群众的需求,拉近非遗与现代文明的距离,使其具有可延续的生命力。
报告提出,加快构建促进非遗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体制机制,进一步搭建平台、创造条件推动非遗融入现代生产生活,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鹿心社表示,要让非遗“活”起来,增强人民群众对非遗的参与感、获得感、认同感,通过“非遗+”的模式,积极探索非遗资源创新转化的路径,增强非遗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产品的附加值,将非遗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非遗保护成果更好为人民群众所共享。
“创新是非遗项目的生命力所在,一定要实现守正与创新的统一。”郑卫平委员建议,要建立对重大非遗项目的精准管理机制,尤其对中华民族所独创、独育、历史文化艺术价值十分重大的、可以作为国家文化标志的非遗项目,实施精准管理,采用各种方式,利用公共媒体力量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传播,进入市场、进入百姓的生活。
人工智能技术在非遗传播中的运用日趋普遍。“从现在情况看,人工智能技术越来越多地用于非遗传播普及,其高效的信息处理、数据推送、图文呈现能力,极大助力了非遗保护传承工作。”方向建议,及时总结推广人工智能在非遗传承传播中的一些好的经验做法,为人工智能更好赋能非遗工作提供参考借鉴,更好地推动非遗保护传承。
“在保护非遗项目时,要有所区别、有所侧重,分类别、分层次积极保护。”地力下提·帕尔哈提建议,挖掘传播优秀文化,要结合时代特点加以继承、发扬、发展,并升华其精神内涵,使之与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使得人们能深刻认识和理解并自觉传承,从文化自觉走向文化自信,增强人们用民间传统文化精髓解决当代面临难题的智慧,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力和向心力。